
读着李默然的《戏剧人生》,仿佛看到曾赋予民族英雄邓世昌的艺术形象以情感、思想、魂魄的表演大师李默然正在天庭之上用他那在《报春花》中注视过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工厂的目光,注视着今天我们急待振兴的中国剧坛。
自话剧传入中国,我们在几十年时间里就完成了对西方戏剧品格的认识,完成了话剧在中国的“本土化”的历史任务,让这门艺术在中国扎下了根,又向着“民族化”迈进。“文革”浩劫以后,话剧再次出发,三十多年来艰难前行,并不断取得成绩。但是与所付出的巨大投入相比,成绩不大,问题不少。当俄罗斯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至今还在上演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百年前导演的《青鸟》的时候,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学习、探索、反思以及一次又一次创新阵痛的中国话剧,却还没有诞生出更多地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演出作品,也没有创作出更多的具有人学内涵的戏剧人物,也还没有创造出几台常演不衰的保留演出剧目。所有当下的问题都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
第一,从“品格与功能”上说,我们长期把话剧当作武器和工具。早在易卜生被引进中国时,他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描写就被忽视了,只把他当作改造社会的利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的“客观化”原则也被抽离了,代之以社会的、政治的倾向性。倡导“左翼戏剧运动”的“剧联”成立时就宣称,演剧是“政治的辅助,武器的艺术,斗争的艺术”。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我们党正处在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剧联”的纲领也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后来虽说在政治上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但是文艺是“政治的辅助”,这个李立三、王明时期的在“极左”路线下提出的文艺口号,到今天已经过去八十五年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清算,至多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换了种种不同的说法而已。当时,倒是没有参加“左翼剧联”的曹禺写出了《雷雨》,开始了《日出》的艺术构思。我们党的文艺专家夏衍同志也是在清算了“左倾”影响之后才写出《上海屋檐下》。
其实政治、军事、历史、哲学、艺术、科技、宗教等,都各有各的对象与任务,都应该平衡发展,不要老是“工具论”,提什么谁为谁服务。如果一定要说谁为谁服务,谁是谁的工具,那么政治与军事才是手段与工具,创建新的社会文化才是目的。新的生产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其目的也是为了创建新的社会文化,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活动的全部内容,最终都是要创建一种文化。对此,周恩来和陈毅同志都曾做过清晰而明确的表述。所以说我们遵循过的“工具论”,不仅提法本身不能成立,而且把手段与目的也给搞颠倒了,从根本上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就难怪我们在这个口号下搞了这么多年,却没有几个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其人学内涵能达到或超过郭、老、曹、田汉、夏衍笔下的人物。今天真的是到了应该彻底清算、否定这个口号及其几十年来的消极影响的时候了。
第三,当时间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话剧工作者面临着急待完成的历史任务:一是研究如何在剧本创作中清除“极左”思潮余毒,摆脱有碍剧本创作健康发展的“工具论”的贯性思维,写出真实、鲜活、生动、丰满的人物,二是开展对表演艺术创作,表演人才培养的规律与办法的研究,三是研究如何拓展美学观念,丰富演剧手段。我们本来应该把这三项工作都当作时代赋予戏剧工作者的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的。然而事实是前两项工作没有做到应有的程度,主要精力放在了第三件事情上。理论研究上,主要研究了演剧美学问题,艺术创作上,主要在进行演剧形式的探索与创新。
如今,又一个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美学探索”与“形式创新”的旗帜下创作出来的戏剧人物的人学内涵,并没有多少能够达到或超过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夏衍笔下人物的深度与丰富性?表演艺术也是一样,新生代演员们的表演水平也并没有几个能够达到或超过李默然、于是之、张伐、石挥、蓝马、孙道临、韩非、舒绣文、秦怡、白杨、张瑞芳、黄宗英等艺术家的水平。
俄国亦曾以剧作形式创新与演剧形式创新当作引领戏剧进步的突破口。然而后来契诃夫在《海鸥》中以特列勃列夫之名说:“关于新形式我讲过那么多的话,可是我现在感到我自己也渐渐滑到陈规旧套上去了。……是的,我越来越来相信:问题不在于新形式,也不在于旧形式,而在于人写作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什么形式,人写作是因为所写的一切自然而然从心灵里流趟出来了。”
人,才是戏剧艺术的对象。写人与演人,才是戏剧艺术的根本创作任务。文学,是演剧的基础;表演,既是演剧这门综合艺术的主体,又是演剧艺术的本体,还是导演艺术创作的主要手段。如果文学与表演这两方面都没有取得真正令人满意的成绩,说我们民族的演剧艺术从整体上进步了,就还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有一位导演艺术家,著名的形式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践的大师,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说,《激流勇进》应该重排,问题不在于新形式,而在于当年的主要人物不够真实。
纵观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是在完成社会学的任务而不是文艺学的任务。因受“极左”思潮和“工具论”影响,真正以人为创作对象与任务的作品本来不多,还大都遭到过否定。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三个时代话剧工作者的创作方向与目的:建国前是为推翻反动统治而进行揭露;建国后是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努力歌颂;新时期本来应该研究人学,表演艺术及演剧美学,但却错失良机,仅仅只是研究了演剧美学,完成了演剧形式的创新创造。
在此我将历史思索引向另一个问题,回顾一下“孤岛”时期戏剧繁荣的原因:一是蒋管势力审查制度的退出,二是党对剧运的领导方针是保存队伍而不是公开斗争,演出中不表达政治思想,三是国人自觉抵制日本势力控制下的电影,日军又从海上封锁了美国电影的输入。于是“孤岛”戏剧迅速繁荣起来。
今天,由于网络的出现已经什么也封锁不了,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结果就出现了拥有诗经与乐府,拥有唐诗和宋词,拥有三国红楼水浒西游金瓶梅的文化大国的新一代国民,因拒绝观看那些花巨资搞出的连主管文艺的领导自己也并非打心眼儿里喜欢的舞台艺术作品于是整天观看韩剧,而且因为看多了还常常互相“阿娘塞欧阿娘塞欧”地打招呼的现象。韩剧、英剧、美剧无非因为描写了人,讲了人的故事而受到喜爱。
今天,已经进入到影视与戏剧成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时代,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今天不能创造出真正受到下一代喜爱的影视、戏剧作品,我们下一代的精神世界就将受到其他民族的塑造。我们再也不能受制于“工具论”了!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再也不能继续自我残害下去了!到了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从剧作上去描写人,从表演上去塑造人的时候了!应该认真考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变目前的现状,敢于壮士断腕,取消对戏剧的控制与利用,还戏剧于人民了!让戏剧去完成它自己的任务,以人为创作对象吧!让作者去写好人,让演员去演好人,由此真正促进戏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吧!
纵观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是在完成社会学的任务而不是文艺学的任务。因受“极左”思潮和“工具论”影响,真正以人为创作对象与任务的作品本来不多,还大都遭到过否定。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三个时代话剧工作者的创作方向与目的:建国前是为推翻反动统治而进行揭露;建国后是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努力歌颂;新时期本来应该研究人学,表演艺术及演剧美学,但却错失良机,仅仅只是研究了演剧美学,完成了演剧形式的创新创造。
在此我将历史思索引向另一个问题,回顾一下“孤岛”时期戏剧繁荣的原因:一是蒋管势力审查制度的退出,二是党对剧运的领导方针是保存队伍而不是公开斗争,演出中不表达政治思想,三是国人自觉抵制日本势力控制下的电影,日军又从海上封锁了美国电影的输入。于是“孤岛”戏剧迅速繁荣起来。
今天,由于网络的出现已经什么也封锁不了,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结果就出现了拥有诗经与乐府,拥有唐诗和宋词,拥有三国红楼水浒西游金瓶梅的文化大国的新一代国民,因拒绝观看那些花巨资搞出的连主管文艺的领导自己也并非打心眼儿里喜欢的舞台艺术作品于是整天观看韩剧,而且因为看多了还常常互相“阿娘塞欧阿娘塞欧”地打招呼的现象。韩剧、英剧、美剧无非因为描写了人,讲了人的故事而受到喜爱。
今天,已经进入到影视与戏剧成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时代,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今天不能创造出真正受到下一代喜爱的影视、戏剧作品,我们下一代的精神世界就将受到其他民族的塑造。我们再也不能受制于“工具论”了!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再也不能继续自我残害下去了!到了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从剧作上去描写人,从表演上去塑造人的时候了!应该认真考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变目前的现状,敢于壮士断腕,取消对戏剧的控制与利用,还戏剧于人民了!让戏剧去完成它自己的任务,以人为创作对象吧!让作者去写好人,让演员去演好人,由此真正促进戏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吧!
纵观我们七八十年来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是在完成社会学的任务而不是文艺学的任务。因受“极左”思潮和“工具论”影响,真正以人为创作对象与任务的作品本来不多,还大都遭到过否定。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三个时代话剧工作者的创作方向与目的:建国前是为推翻反动统治而进行揭露;建国后是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努力歌颂;新时期本来应该研究人学,表演艺术及演剧美学,但却错失良机,仅仅只是研究了演剧美学,完成了演剧形式的创新创造。
在此我将历史思索引向另一个问题,回顾一下“孤岛”时期戏剧繁荣的原因:一是蒋管势力审查制度的退出,二是党对剧运的领导方针是保存队伍而不是公开斗争,演出中不表达政治思想,三是国人自觉抵制日本势力控制下的电影,日军又从海上封锁了美国电影的输入。于是“孤岛”戏剧迅速繁荣起来。
今天,由于网络的出现已经什么也封锁不了,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结果就出现了拥有诗经与乐府,拥有唐诗和宋词,拥有三国红楼水浒西游金瓶梅的文化大国的新一代国民,因拒绝观看那些花巨资搞出的连主管文艺的领导自己也并非打心眼儿里喜欢的舞台艺术作品于是整天观看韩剧,而且因为看多了还常常互相“阿娘塞欧阿娘塞欧”地打招呼的现象。韩剧、英剧、美剧无非因为描写了人,讲了人的故事而受到喜爱。
今天,已经进入到影视与戏剧成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时代,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今天不能创造出真正受到下一代喜爱的影视、戏剧作品,我们下一代的精神世界就将受到其他民族的塑造。我们再也不能受制于“工具论”了!我们在艺术创作上再也不能继续自我残害下去了!到了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从剧作上去描写人,从表演上去塑造人的时候了!应该认真考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改变目前的现状,敢于壮士断腕,取消对戏剧的控制与利用,还戏剧于人民了!让戏剧去完成它自己的任务,以人为创作对象吧!让作者去写好人,让演员去演好人,由此真正促进戏剧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吧!
李默然为了寻找具有中国韵味的表演中国的题材与人物的创作方法,借鉴戏曲的手法进行话剧、影视表演的尝试。这种尝试,或成功于电影《甲午风云》,成熟于话剧《第二个春天》,在话剧《报春花》的表演创造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最后在《李尔王》的表演艺术创造中又证实了这样的表演方法,不仅可以完成对中国题材和中国的“历史人物及现代人物”的表演创造,也可以用来完成最具典型意义的西方剧作中最为重要的人物的形象塑造。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中国的民族话剧终有一天对世界演剧艺术做出我们独特的中国式创作方法的整体贡献时,在其重要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组成部分中,必定不能缺少李默然先生的那些蕴含着东方戏曲美学神韵的表演艺术经验!
2024-10-16 14:36:39
2024-10-16 14:35:51
2024-10-15 10:14:13
2024-10-15 10:12:30
2024-10-15 10:09:31
2024-10-15 10:08:10
2024-09-09 15:2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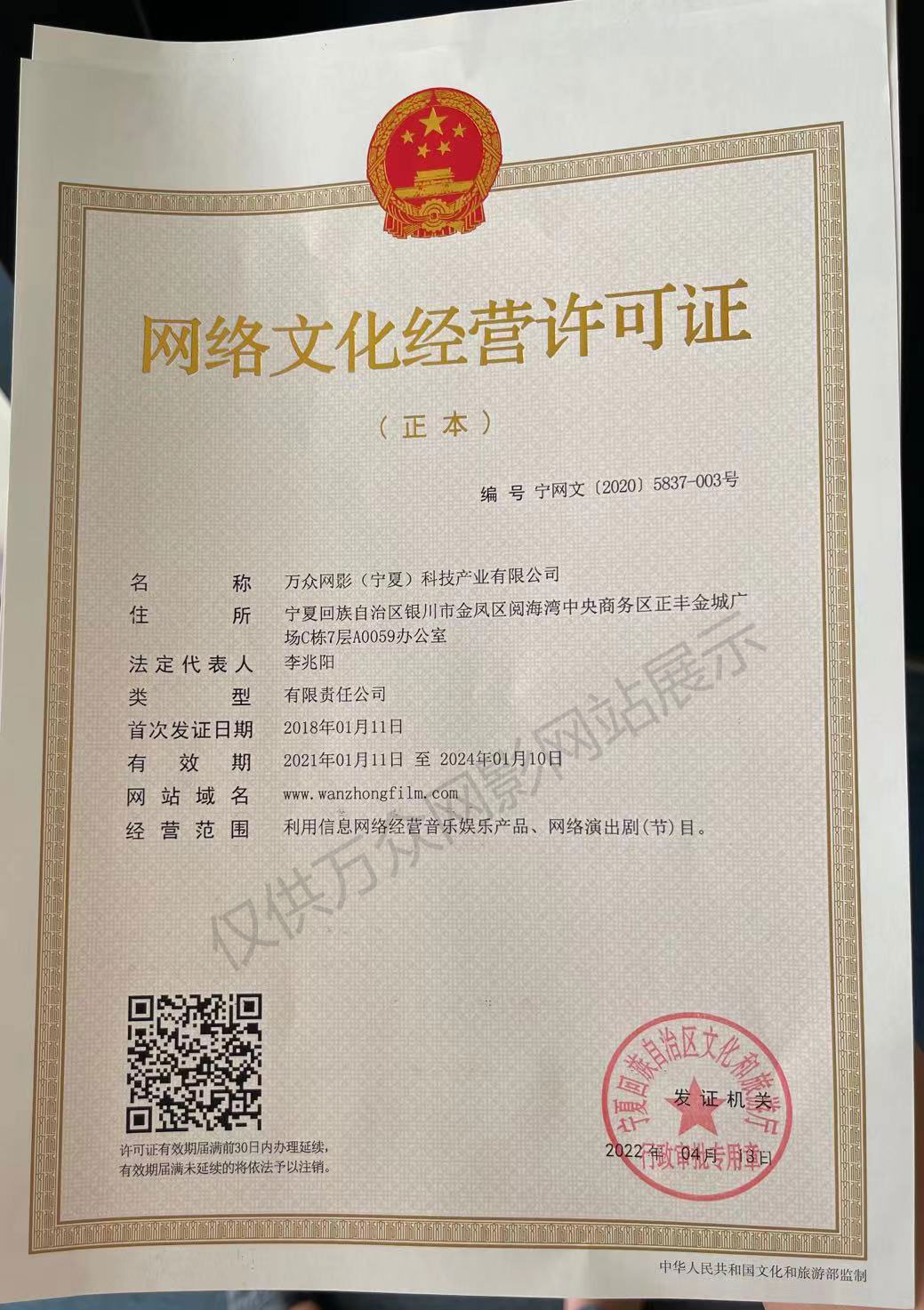 ×
×
 ×
×